与杨澜的慈善对话:更想谈的是捐给谁、怎么捐(2)
大多数“诈骗捐款”并非恶意
《环球》:这次“慈善之旅”是否会引发官方层面对慈善体系的思考? 比如改革税制、加大捐赠激励力度,或者改善慈善机构的管理?
杨澜:这也是我们的慈善晚宴和两位先生过去在美国举办的慈善晚宴的不同之处。 他们在美国的晚宴确实只邀请了一些亿万富翁及其家人参加,但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们不仅邀请了财富榜上的企业家,还邀请了活跃在慈善榜上的企业家。 慈善家方面,我们还邀请了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突出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民政部门的高级官员。 我们只是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多个阶层的合作,而不是某个人群的专有权利或特权。
那么说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我认为有两个,我想这两个问题都引起了在场的民政部高级官员的关注。 一是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我们特别希望尽快出台《慈善法》,对慈善事业做出明确规定。 第二个瓶颈是目前慈善机构的专业化水平明显不足。 那么,当一个慈善机构非常弱小,财力较差的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们的慈善愿望和捐赠意愿。
《全球》:随着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公益事业越来越受到多方关注和监督。 “虚假捐款”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现象慈善机构的英语,尽管大多数事后都得到了澄清。 但这反映出公众对当前慈善筹款的一些质疑。 对此,除了加强适当、必要的监督机制外,还应该做哪些建设性的工作来提升公众的慈善意识? 认同感?
杨澜:我认为,如果我们分析过去发生的几起所谓的“诈骗捐款”事件,大多数都不是恶意的“诈骗捐款”,而是出于善意的捐款承诺。 然而,由于缺乏后续、跟上,结果是与公众的期望存在差距。 并不是当事人想将公众的捐款据为己有。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但由于团队疏忽跟进,涉案人员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可能会导致这种尴尬的局面。 这仍然是目前大家都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请专业的团队去做专业的事情了。
例如,巴菲特先生在一次慈善晚宴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如果我想拔牙,我不会自己用钳子拔。 我必须找一位有经验的牙医。 我认为比尔盖茨做慈善比我做得更好,所以我给他钱去做。 我想知道我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很多明星、名人还抱着“我捐钱,我自己团队执行”的相对基本理念,可能很难保证运作的专业性。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同意企业家带着现金去灾区,把几百块钱塞到每个人手里,因为这种做法的效果也很难衡量。 所以我还是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慈善机构能够变得更加专业,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给他们钱,他们也会告诉我们钱会用在哪里。
其实,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先生这次来中国最大的感悟就是,在美国,你想捐钱,只要你愿意捐,因为有很多非捐献者。政府组织数量众多且相对高效。 组织开展这些捐赠活动。 但在中国,公益组织力量相对薄弱,专业性也相对薄弱。 所以,问题不是你愿意捐多少,而是这些组织能帮你落实多少。
慈善事业注重可持续发展
《环球》:您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什么样的慈善文化?

杨澜:我认为中国的慈善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是时候大放异彩了。 我希望中国的慈善事业像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 不仅十分密集,而且种类丰富、层次丰富,相得益彰。 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它无法主宰世界。 它必须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 慈善机构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比如我们阳光文化基金会四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资金、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就决定专注于慈善文化。 宣传推广,以及慈善能力培训。 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有资源优势,所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选择专注于救灾、扶贫等领域,这些领域也很重要,但不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慈善需要全面发展,同时每个慈善基金会需要在各自的领域找到自己非常清晰的定位。
《全球》:国内慈善事业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您认为各类慈善机构应如何完善自身发展模式,以更加务实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优质的慈善服务?
杨澜: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 我发现很多慈善机构仍然陷入“从手到口”的模式。 他们在有了收入之前不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 只是“乞讨”得到一点钱就马上花掉,缺乏长远、系统的计划。
我们社会什么时候捐款热情最高? 救灾期间。 但在国外社会,比如在美国,救灾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民间组织很少做救灾工作。 那么,更多的私人机构在做什么呢? 教育、艺术、科学研究和宗教是捐款最多的领域。 因此,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并且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我们很多公益组织,在大灾难的年份,捐款会增加百分之一。 一百次,但是在没有灾难的时候,他们的日常维护似乎很困难。 在这种又饱又饿的状态下,很难保证组织长期良好运转。
所以,我们现在的慈善状况,体现了一个不可预测的情况,而且随着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波动性很大。 在一些比较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普通捐助者,他们每个月可能只捐出10美元,但他们会持续这样做一辈子。 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灾难的时候就捐一万元,但平时可能不会捐。 所以这种慈善环境和氛围是不一样的。
《环球》:那么与杨澜的慈善对话:更想谈的是捐给谁、怎么捐(2),李连杰的“一个基金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吗?
杨澜:是的,因为他觉得大家的参与比筹集多少钱更有意义。 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发展慈善事业不是某个阶层、某个小团体的权利。 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
慈善不是临退休时才做的事
《环球》:您认为慈善机构如何扩大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杨澜:我觉得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包括专业人士进入慈善领域,这方面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例如,阳光文化基金会今年将启动一个新项目。 我们邀请在世界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位的企业管理者利用业余时间作为志愿者与公益机构的管理者进行交流。 管理经验,我觉得这样的互动也是一种慈善。 慈善不应该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形式。 然而,或许各慈善机构共同呼吁的,是中国《慈善法》的早日颁布。
“全球”:慈善是全球性事业,但各国管理机制不同。 您认为什么样的机制适合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
杨澜:我举几个目前基金会遇到问题的例子。 我认为《慈善法》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大家才不会感到困惑。
例如,第一,捐赠证券是否可以视为捐赠。 比如,一个企业家将自己的公司上市,并捐赠自己的股份成立基金会,那么根据现行的基金会管理规定,这些股票必须兑现才能算作捐赠。 的。 但同时,证监会也要求大家不要一下子将股票全部抛售,因为这会引起股市的大动荡。 但如果你回顾一下,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捐赠主要是证券。 巴菲特并没有卖掉所有股票套现,而是将所有现金交给了比尔·盖茨。 事实上,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有两个机构。 他的左手是捐款,右手是资产管理机构。 它还负责每年进行投资以获得股息或收入,以维持整个基金。 将正常运行。 所以他也需要一个投资机构来保值增值。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立,以及如何确定其性质慈善机构的英语,需要通过法律来更加明确的规定。
第二,现在的基金会,当你吸收捐赠,第二年捐赠产生了增值,那么这部分增值就要缴纳企业税。 有的企业家会说,我已经把这笔钱捐给慈善基金会了,为什么还要按照企业标准对年收入征税呢? 这公平吗? 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大家来解决。
第三慈善机构的英语,什么样的基金会有资格进行相对独立的公开募捐。 前一阶段,李连杰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因为他希望成立一个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而不隶属于任何基金会。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空缺。 因此,大多数公募基金会必须隶属于具有公募资质的大型基金会的法律和财务管理方能运作。 你无法独立运作。
为什么大家都希望制度上有突破,因为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角度明确界定。 当然,政府部门也会有一定的困惑。 例如,如果捐赠证券可以免税,那么有人会在这里洗钱吗? 有些人会逃税吗?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做出权衡。 逃税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与为社会提供公益这样的积极效益相比慈善机构的英语,哪一个更重要呢? 当你需要承担某些社会风险时,这个风险值得吗? 如果有这样的风险,你总不能不这么做吧? 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希望有明确的游戏规则。
《环球》:这是逐步完善中国慈善事业的必由之路。
杨澜:是的,美国实际上花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不断完善慈善法。 其慈善法一开始就存在一些漏洞,使其成为逃税和洗钱的场所。 但问题不断被发现,不断修订,目前其慈善立法已较为完善。
我觉得比尔盖茨这次提出的想法非常好。 他说,以前我们往往只有退休或者快去世的时候才会想到做慈善事情。 其实慈善是可以从小开始慢慢开始,不断积累经验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做慈善永远不嫌晚,但宜早做。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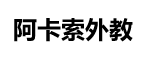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