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热三十年 当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什么

1984年,上海各高校研究生在联谊活动“英语角”上英语热烈交流。(南方周末供图)
20世纪80年代学英语,流露出长期封闭的中国人对英语世界的好奇;90年代学英语,则如《北京人在纽约》一样,弥漫着文化冲突的焦虑;2008年以后学英语,则流露出“想把中国的繁荣昌盛传给外人”的骄傲。
“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制作的吗?”
1982年1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局(现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张象山走进中央电视台电化教育部办公室询问。
许雄雄主任和同事们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晚上18点20分,他们改编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以下简称《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许雄雄结结巴巴地承认,节目是利用英国BBC的现成材料编的,“没用外汇,只是花了一些人民币。”同事正要过来打圆场。
“看到了。”张象山转身离开,留下两个字,“很好!”
没人能预料到它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中国日报》当年报道称:“该节目在中国拥有 1000 万观众,与该国现有的电视机数量相同。”

政治阴云刚刚散开一道小缝,学习英语热潮便席卷了全国。
随着出国潮的兴起和考试制度的确立,这股热潮被这片久旱逢甘霖的土地吸收、固定下来,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一道不变的风景;而回首三十年过去,热潮之下的暗流似乎很早就显露出苗头。
“要一杯杜松子酒吗?”
凯瑟琳·弗劳尔1981年9月来到北京。这个说话慢条斯理、一头红发的伦敦女孩后来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华克琳。
仅仅三年时间,这个大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学英语听什么歌,国家公派留学考试恢复,中国向41个国家派出了480名留学生。当50多名公派留美学生参加卡特夫人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时,他们在服务台上连大衣的主人都分不清了——所有的西装、毛呢大衣都是教育部出资定制的。
当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衣上时,时代的变化已无法阻挡。1978年,《北京日报》刊登文章,呼吁“努力掌握外语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同年,科学大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融入渠道一经打开,便迅速扩大。到1985年,中国公费出国留学人数已达2万人。更重要的是,华克林来华的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暂行条例》,这才真正点燃了这股热情。托福考试人数从当年的285人迅速增加到1986年的1.8万人。
1981年,首批公派留学生胡文中从澳大利亚回国,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出国前,他在建国饭店的外语教材发布会上,把公众对英语教材的期待形容为“等着米煮熟”。如今,机会就在他面前:许雄雄在考察BBC时看到了《追随》的样片,便邀请老同学胡文中和前法语版主持人华克林一起制作该节目的中文版。

《追随》卖到日本时,获得了数十万英镑的收入;英国方面猜测,封闭已久的中国不会接受一部充满西方生活方式的教育片,因此只要求几千英镑,并意外地获得了批准。
《他》首播当年学英语听什么歌,中国已有29个县市对外国游客开放,松下等国际巨头相继入驻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亟需语言搭建桥梁。《他》由此创造了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奇迹。
由于随附讲义的出版,《电视周刊》订户一下子增加了50万;正式出版的教材第一卷销售数百万册;远在乌鲁木齐的观众也亲手编写了节目脚本,并附加图片;二机部自发成立了“跟随”学习小组,把节目录制下来,反复听看,模仿表演,还专门邀请胡文中前来观摩。
学习英语热潮也得到了高层的支持。邓小平指示说:“要派几万名留学生出国学英语听什么歌,而不是几十名。”要摒弃极“左”思想,“留学生管理体制也要改革”学英语听什么歌,“不能搞得那么死板,要多和别人相处,才能学到东西。”
高层领导人的意志有力地推动了这个集体主义国家走向开放,“两人必须一起出门”、“不准播放非新闻类电视节目”等规定逐渐被取消,学习英语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追随》播出的那一年,来自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年轻战士董立正因为英语学得好而上了《新闻联播》;在对“青年先锋、时代楷模”张海迪的宣传中,经常可以看到她自学英语、德语、日语、世界语的故事。
1984年,英语被列为高考主修科目,两年后,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挂钩。
在冰雪开始消融的岁月里,《他》也成为人们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扇窗口。在呼和浩特的一家酒店里英语热三十年 当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什么,服务员问华克林:“您好,要来杯杜松子酒吗?”这位伦敦女孩最终还是要了一杯茶——当然这里没有杜松子酒,服务员只是在练习节目里的台词。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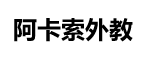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