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念博士 我每天在跟法语搏斗|三明治

文字|丽贝卡
编辑|珍妮
今天是第一堂课。根据会议怎么练口语,请简要介绍自己,并告诉我为什么要参加法国课程。丽贝卡,让我们从你开始!”
“呃……大家好,我是历史系的丽贝卡。我以前曾学习过法语,但是我上大学后我还没有碰过我。我计划以后在法国学习,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深入学习。”
“哦,真的吗?非常非常困难,你必须努力工作。”
在听到老师的回答之后,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我说了一些不现实的话。实际上,当我张开嘴时,这些句子无法控制地从我的嘴里滑了出来。当我感官时,为时已晚。幸运的是,老师不再问我最担心的问题:您为什么要在法国学习?
我编织了无数的看似完美,但是这个问题的无聊答案是因为很难说出真正的答案。当我15岁那年,我不小心看到一位作家在电视上告诉她她在巴黎旅行,这记录了她在餐厅里吃的东西,她在路上和她住的房子里的长度。 ,但我并没有被她的故事所吸引,我什至不记得那本书的标题是什么。真正感动我的是她拍了一张黑白照片,一个长发的女人坐在照片中,看着塞纳河,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就像一层近乎透明的面纱。我无法确切地回答这张照片给我的方式,但是女孩的外表和阳光明媚的塞纳河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样,我觉得我长大后,我必须去这个地方看它。我不仅洗脑了自己怎么练口语,甚至告诉我的同学,我将来会去这个国家学习。这个近乎疯狂但不合理的想法使我开始在高中读法语。
如果您用个性来描述法语,那么当我第一次见面时,我对此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要求很多。我第一次了解到语言具有性别。法国名词被分为负面和阳式姓氏,但是老师无法回答为什么桌子是负面的,而猫是积极的。我第一次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表达数字的方法。事实证明,法语中70的表达是60加10,而80是4倍20。但是,法语的难度远不止于此。最让我震惊的是动词变化是如此精致,几乎被变态了,这让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对时间特别敏感。

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了老师讨论论文,老师问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我根本没有看到本章的女演员。他们都是其他人的讨论。他们去过哪里?”
“我真的找不到他们的声乐记录,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只能从别人的角度写下……”
“那他们为什么失去声音?”
在我告诉老师一些猜测之后,她说这就是你想写的。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您始终想编写与其他学者相同的内容,但您不是他们。尽管他们都是研究女演员,但它们之间遇到的情况并不总是相同的。事实证明,我一直在努力模仿他人,例如在撰写论文时,在我一生中的其他时刻也是如此。
当我第一次进入博士课时,我周围的人总是提醒我更多地社交并结识尽可能多的人,这对未来找到工作非常有帮助。除了建立联系外,我们还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制定工作计划。 KPI指标参加研讨会,发布论文和申请奖学金的指标。我根据需要接受所有这些建议,我会做任何其他人的建议。我天真地认为未来会像计划一样顺利,但是我不知道该计划永远不会赶上变化。
这种流行病的突然爆发使我无法去任何地方,所以我只能坐在家里。我很乐观,认为还可以,至少我仍然可以检查材料并在计算机前阅读文献。可以说我的日常工作既简单又无聊。早上起床并吃早餐后,我100年前开始阅读电影,杂志和报纸。我做了一张特别的桌子。有将近400本书要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我只是潜入了这样的巨大而复杂的信息海洋。我经常看到我忘记了时间。当我回到感官时,我发现太阳即将落山。当时,我就像荒野中的一个挖掘机一样,希望能在这个宽敞的开放空间中挖出黄金,但没有发现黄金,但该人被困在里面,无法下车。
这项研究进展不顺利,我感到焦虑。我以为我投入了足够的时间,所以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取消原始的休闲和娱乐。逐渐地,只有论文留在我的大脑中,而我无法容纳其他论文。某事结束了。有一天,我真的无法忍受内心的兴奋性,我渴望与某人交谈,但我不知道我能告诉谁。绝望地,我试图第一次预约心理咨询。由于流行病,我们在线见面。打开相机后,我以为她会先问我有关咨询的动机,但她没想到她只是轻声说:“你还好吗?”听到这句话我当场哭了,真是太普通了。这是我成年时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泣。
我真的不记得我在第一次咨询中所说的话,因为我哭了很长时间。当时,各种压力均同时交织在一起。除了学术压力之外,让我最痛苦的是,我无法融入学校环境,并严重适应了法国生活和工作效率的适应性。在来法国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具有高压力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生存,但是在我来之后,我经常被琐碎的事情击败。我不知道我在哪里错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很好,但是我很脆弱。我只记得在咨询之前,我不禁对顾问说:“我真的想逃离法国。我不想再说法语了。”

“来吧,跟着我再次阅读这句话,您必须练习法语发音的清晰度。”
“ J,我今天要练习讲话,而不是练习口语。我可以完成练习吗?”

“不,你是一名博士生,不是法语的初学者。你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只说法语,但你必须说漂亮的法语。”
J要求我打开YouTube页面,为我找到几首法国歌曲,并请我回家并唱歌,直到它们与原始歌手完全一样。完成作业真的很烦人!
我在公共福利协会中遇到了J。这种关联最初是在巴黎学习的德国人的接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发生了争执。战争结束后,一些民间组织开始恢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该协会在此背景中。下一步出生。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法国学习,该协会只是向外界开放。只要支付一年的注册费,任何国籍或年龄的外国人就可以加入。这里的大多数志愿者都是退休的法国老年人,他们每周预留一到两天,来这里练习口语或帮助我们校对论文。 J是突尼斯的志愿者之一,是法国在北非的前殖民地之一。在一群白发志愿者中,他特别明显,皮肤深色和秃头。尽管J帮助我几次纠正了我的论文,但他不喜欢像其他志愿者那样分享他的生活,所以我对他不了解,只知道他以前是建筑师。当他帮助我们修改论文时,他充分利用了建筑师专注于结构和美学的精神。为了调整句子,他可以花近一个小时让所有人抱怨,但他必须承认,在他的指导下,J的写作技巧非常好,我的毫无生气的论文似乎注射了活力,这些台词充满了。活力。
回到家后,我播放了J在我房间的计算机上指定的歌曲。这是1980年代的一首古老歌曲。歌词告诉恋人的渴望。听着低声喊着的女歌手,我的想法慢慢地浮出水面。到目前为止,我最后一次唱歌是多久以前?搬进新公寓后,这里的隔热材料非常好,以至于我可以毫不动摇地发出声音。我试图哼着几句话,但是我的唱歌听起来很奇怪,好像有一块布遮住了我的嘴,而且语气像雾一样朦胧。

“我听说人们会说不同的语言,他们的声音会变得不同。”
“是这样吗?我从未注意到它。”
“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上课了。在说法语时在法国念博士 我每天在跟法语搏斗|三明治,您是否仔细听到自己的声音?”
课程大约5分钟路程,我坐在教室里做功课。佛罗伦萨突然从讲台上出现。她调整了设备,同时问我这个奇怪的问题。佛罗伦萨是发音课的老师。她来自波尔多,头发很短。她大部分时间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并且下课后总是会留烟。她看起来很酷,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当我们向她抱怨学习法语有多困难时,她都会看着我们,就像她在看着刚进入幼儿园的小儿子一样,她的善良忧虑。 。
发音课堂教室是一个大型的视听教室,带有计算机,每个座位上的耳机和会议麦克风。在佛罗伦萨的指示下怎么练口语,我们戴上耳机,阅读麦克风中听到的句子。当耳机中的声音结束时,她向我们发出信号,摘下耳机,笑着说:“下一个是这堂课中最可怕的部分。我会记录你们每个人的声音,我将稍后再播放。太尴尬了。佛罗伦萨说,这不是关于谁发音最好的,而是要让我们张开耳朵并听到我们从未关注的细节。我以为我对自己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当我听到自己说法语的剪辑时,我感到震惊。扬声器稍微嘶哑和厚实的女性声音。她的节奏显然比其他节奏快的速度要快,她听起来有些焦虑。如果我没有用自己的耳朵听到它,那我就不知道那是我的声音,这与我说的中文完全不同。我觉得像一个说法语的冷酷人,我觉得我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并且与所有人保持距离。当时,我的法语不太流利,只是在考虑如何快速提高我的语言技能。我不知道是否是这种情况,这使我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狭窄。除了法语外,我不想知道什么,因为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力量消失了。现在回顾过去,当时我觉得自己像是登山者,渴望征服法国山。我只想尽快到达顶部,我不在乎沿途的风景。

“害羞……abla…ms。,请去柜台17号”
“害羞……abla…ms。,请去柜台17号”
“最后一个电话,害羞……abla…ms。,请前往柜台17”
扬声器发出了快速的声音。在我识别此名称的音节之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广播其他名称,这意味着害羞……ABLA…MS。错过了交出文档的时间。我旁边的阿拉伯奶奶互相看着对方,他们同时痛苦地微笑。只有那些坐在移民警察局大厅的人才能理解这种默认的理解。我看着墙上的时钟。早上只有九点钟。大厅里到处都是人。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个独特的法国纸质文件夹,其中充满了更新和续签许可证。文档。候诊室非常安静。除了偶尔会哭泣的孩子,几乎没有说话的声音。每个人都盯着挂在墙上的扬声器,希望很快听到他们的名字。 。
对于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来说,每年最痛苦的事情是去移民警察局更改其居住许可。一般而言,我们需要预约向我们在居住许可到期前三个月居住的派出所向派出所支付信息。在约会当天,指定的文件将移交给派出所柜台。柜台工作人员审查它后,他们将提供临时文件。居住,等待新的居住卡完成,然后预约去获得卡。尽管更新拘留的程序相似,但每个警察局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居住的区域需要在警察局的官方网站上预约。任命过程经常让我反思为什么我来法国学习。根据官方声明,他们随机打开预订时间。该句子的浅行是:“您是否可以预约完全取决于运气。”每年6月底,当我经常去教堂时,我将在捐赠盒中扔2欧元硬币,点燃细长的白色蜡烛,站在圣母玛利亚枯萎的雕像前,真诚地祈祷,希望这一点她可以祝福我成功地改变了居住。预订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周内,我只专注于一件事:继续刷新官方网站页面。终于得到约会后,真正的困难仍在领先。
我家中的移民警察局很大。穿过大门后,您会看到一栋大约20个故事高的银建筑。建筑物后面有几座建筑物看起来非常技术。首先,那些改变住所的人将直接走进银建筑。进入大门后,经验丰富的人将走到左侧和底部。有一栋灰色建筑,只有两层。当您走近时,您会看到墙壁。有一个不起眼的标志,上面挂着“外国接待处”一词。在门口有几名认真的警卫,他们在驱车未约定的人时检查了我们的约会通知。进入后,每个人都直接前往右侧的小型蓝色柜台进行报告,然后去大厅等待楼上的工作人员播放电话。有一排白色计数器怎么练口语,二楼有数字。一块透明的塑料板位于柜台上。工作人员坐在塑料板后面。从小蓝色计数器收到通知后,他们将使用桌子上的麦克风阅读“ XXX/MS。在不到三遍之后,当场约会无效,因此这个滚动呼叫过程总是会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和害怕。单词“计数器”。名称中的第一个音节清楚,其余的单词似乎在他们的嘴里,这听起来很模糊。

像往常一样,我打包了我的东西,修改了论文后离开。协会主席L,叫我
“您想成为协会的学生代表吗?”
“啊?我?为什么?”
“当前的学生代表正在搬到其他城市,无法再次来到协会。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来接管他的职位。我认为您很容易相处,其他学生喜欢谈论对您来说,这样的人非常适合成为学生的代表。
“学生代表应该做什么?”

“没有什么,主要是参加该协会的行政会议,并成为志愿者和学生之间的通讯桥梁。”
“但是我的法国人不是很好。”
“那是不对的。您可以在会议期间练习法语!”
在说这句话之后,我非常困惑地同意,所以我仍然犹豫。
在去地铁的路上,我与我的朋友谈过了这一点。我想知道我是否认识到错误的人,因为协会中有许多亚洲女孩,而且我们的外表出奇地一致。每个人都有长长的黑色直发和脸。戴着一副镜头略厚的眼镜。我的朋友轻易地说:“我们已经在协会中呆了很长时间了。你仍然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其他法国人的眼中,亚洲女孩看上去也一样,即使他们是困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L今年将近80岁,有着漂亮的肩长头发,她总是像小女孩一样在头发的两侧戴发夹。 L退休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不知道是否是这种情况。她非常擅长与人聊天。当我和她说话时,我感到非常放松。我不像我在学校那样紧张。我什至可以平静地表达我通常的习惯。负面情绪敢于表现出来。 L是协会主席,似乎整天都坐在接待台后面处理文件,但实际上,他像人类学家一样观察我们。她从来没有称学生的名字错误,并且知道每个人的国籍,个性特征,甚至是论文的标题。我无法想象如果缺少该协会,该协会将会变得什么。事实证明,我已经将这个地方视为我在法国的第二所房屋,但不知道。我只能在这里毫不动摇。
也许是出于对L的信任,我成为了学生代表,从那以后,我为协会添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法国人。当我试图从他们的角度看我周围的人和事物时,我突然意识到许多误解不是由语言障碍引起的,而是由双方的不同思维逻辑引起的。一段时间以来,我说的最常见的句子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吗?”神奇的事情是,当人们听到这一点时,无论他们是生气,恐惧还是焦虑。我可以看到不安的表情从他们的脸上闪烁,立即措手不及。事实证明,理解比语言更重要。我不再注意自己的发音,使用单词并同时接受单词,同时接受自己会犯错的人。当我将法语视为终生学习时,我与它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张。
有一天,我照常上了地铁去上学。下午3点在马车上没有人。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用耳机听了收音机。在节目结束之前,电台DJ播放了魁北克乐团幽灵之吻覆盖的法语歌曲,主唱轻轻唱歌:“太阳不知道)这显然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康复的。我坐在学校对面。在我拿起背包时,替补席的另一端没有注意到替补席的另一端。
她说:“你唱歌很好。”
写笔记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与我生病并赶到纸上的时间相吻合,所以我只能在上床睡觉前慢慢写下来。感谢Jenny帮助我找到一个主轴,我可以用一堆混乱的单词进行讨论。

这个故事由短篇小说学院的导师完成
从2月16日至29日,新的短篇小说学院将开始
单击下面的迷你程序进行注册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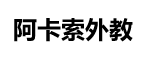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