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青年作家颜歌,写一本书保管一代人的记忆

《我的天才女友》
这些年来,严歌一直在写作,在行走。她年轻时就出名了。在华人世界工作多年后,她来到爱尔兰,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并在英语文坛崭露头角。去年冬天,作家严歌带着失踪多年的中国新小说《平乐县志》归来。
严歌十多年来一直在书写《平乐镇》的故事。这个拟态的故乡,一直寄托着她的乡愁,见证着她的成长。在不久前揭晓的第九届单程街书店文学奖中,严歌凭借《平乐县志》荣获2023年度青年作家奖。

严歌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道:“前两天,我看到了和我一起提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对能上这个榜单感到特别荣幸,也对这个榜单本身感到兴奋。”
我们的写作来自不同的地方和土壤年度青年作家颜歌,写一本书保管一代人的记忆,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中。我们用多样多样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视角来讲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故事。这个热气腾腾的文学世界正是我一直以来对文学的想象,也是我写作的最大理由。我们的语言是用来表象和表达的,但它也隐藏着陷阱和枷锁。文学虽然源于语言,但它也是让我们超越语言及其局限性的方法。文学不仅为我们照亮了已知世界中被忽视的角落,而且引导我们到达我们以前从未想象过、也不知道我们能到达的崇高境界。 ”
播客《Out of Time》前不久还邀请了颜歌做客。她们从严歌的身份转变入手,讨论了写作、女性身份、移民、语言等诸多问题。本期内容由乌托邦授权转载整理。
以下内容整理自播客《Out of Time》。该内容已被删除。欢迎您扫描下方二维码收听完整音频。
英语赋予我非常奔放的性格
不合时宜: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新概念时期第一次认识颜歌的。那一代新概念作家中有多少人还在写,其实很难统计,但严歌一直在写。现在我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进行各种探索,重新发现新的空间身份。我认为这需要很大的韧性、对写作的热情、大量的天赋和努力。我其实很好奇你用英文写作的五年里,这种转变是如何逐渐发生的?中间经历过一个过程吗?当你第一次开始学习英语时是什么感觉?
严歌: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和身体上的我。生活中,在语言方面我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有人会问我,你做梦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当使用语言,尤其是英语作为一种后殖民语言时,人们有时会下意识地想,你有权利说这种语言吗?或者你在这个语言位置上处于什么位置?人们会想象一种垂直的权力等级制度,以母语人士为最高层。所以人们会不断地将自己与这个标准进行比较。

《前世今生》
这个关于睡觉和做梦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你的英语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和语言有关系,包括我和四川话的关系、我和普通话的关系、我和英语的关系。 ,其他人与自己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们既是公开的,也是私人的。在英语方面,我从来不会将自己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比较。我教写作,90%的学生都是以英语为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英语问题。这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人对语言的敏感度或者语言对你的重要性。
我先说一下个人吧。我觉得我用英语更轻松了。在英语中我可以很狂野并且毫无歉意。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你似乎突然不再具有传统东亚女性的身份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年轻女人。这两件事在中国语境下会产生一种始终伴随着我的顺从感。
当我第一次接触英语时新概念英语好吗,大多数事情都是学术性的。当时我去美国读博士,还没毕业。因为我是一个对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所以我开始喜欢看英文的东西。我发现英文的相关内容更容易理解。所以对于英语来说,我个人对意义动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学术性的,非常接近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我进入英语方式,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理性的语言。我用它来表达更多的学术或智力思维,这是去女性化的。

当然,汉语也可以做很多英语做不到的事情。这一直是我的痛苦。我也很想用中文写东西,比如背古诗词。这东西只有中文才感觉舒服。我想从一开始,当我拥有英语的性格时,那是一种比较奔放的性格。我可以说任何我想说的话。我作为非母语人士的身份给了我很大的通行证。
我开始写作,我的英国性格就变成了作家,大概是在我的英国性格确立并占据了我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至少有一两年,我能感觉到英国人的性格主宰了我的生活。因为你平时和别人讨论的一切都是用这种语言发生的,那么到了某个时候,它肯定会渗透到你的写作中。事实上,开始用英语写作一直是我所抗拒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写作领域应该用中文,但最终没有办法。我身上的肿瘤越来越大。我有一些感受、想法和想要用英语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些表达必须用英语表达。

《前世今生》
当然,第二语言也有很多困难。有时候反思一下,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把这些困难放在一边不说,但这其实是不公平和虚伪的。它当然有很多困难和很多限制。例如,我今天早上去城里,回来的路上正在听小说。小说里有很棒的对话,非常口语,身临其境。我突然感觉很痛苦。作为一个作家,无论我怎么用这种语言写作,我都写不出这样的对话。例如,我不可能写出两个来自都柏林南部的歹徒之间的对话。我可以用中文写这种对话,但我永远不能用英文写。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生活中,我不常有这样的感觉,但在写作中,我经历了很多持续的痛苦和挣扎。
我想我之所以暂时不想写中文,是因为写完《平乐县志》之后,中文就没有太多的痛苦和挣扎了。从技术层面或者故事进展层面,你能感觉到你其实已经变得更加熟练了。摩擦和挣扎大大减少了,这让我对它的兴趣降低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寻找痛苦和纠结的过程。
做母亲 vs 做作家
Out of Time:当我们第一次开始录制节目时,您描述了您的一天并谈论了很多有关如何与孩子打交道的事情。所以我猜你现在的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我记得你之前回答过“你有没有考虑过写一本以母亲为角色的书?”你的回答是“还没有”。我想问你现在感觉如何。您打算以母亲的身份写一本书吗?
雁歌:我写的东西里有一个母亲的身份。主角是一位母亲,但她是一个逃离了母亲身份的人。这是我特别想写的,也有点忌讳。我觉得很多女性成为母亲后,母性就变得比你个人更重要。 “个人的你”必须做出牺牲新概念英语好吗,为“母亲般的你”让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每时每刻”
但很多人都有理由做出不同的选择。我现在写的东西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线索和情感。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之一是我想写一个抛弃孩子的女人的故事。但我不能说这个女人是受害者,而是必须以作者的身份克制自己,为她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伦理和社会评价体系。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那就是她个人的挣扎或者纠结了。
相应地,在许多文学叙事、神话故事或民间叙事中,男人遗弃孩子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他能离开家很多年,这和他的父亲身份无关。包括大禹三度过屋不进的故事,这都被赞为美丽的故事。我对这两种叙述以及它们背后的伦理道德差距非常感兴趣。当我写一些东西或进入一个项目时,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必须尝试一下。我想写一个不需要解释或道歉的女人,但她作为个体的挣扎肯定与母性有关。这样,你就会感受到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性别叙事,因为对于男性来说,不仅不需要解释,而且根本不需要提起。这种比较让我觉得很有趣。当然,挑战在于大家能否接受这种事情。
这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小说里有妈妈吗?现在我们有了,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感觉。这是一个不是母亲的母亲。我觉得文学归根结底还是要表达这种灰色的、多样的、复杂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但是伟大而优秀的小说家所能描述的人性的微妙之处是很难用语言直接表达出来的,而这样的东西一旦描述出来,就会成为很多其他人的故事和故事。 。叙事可能是一种个人的历史,或者是一种自我的叙述,它会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光芒。最终,我希望表达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的各种状态,或者作为一个母亲的状态。

“每时每刻”
我有一个习惯很多年了。我实际上不会写我周围的人,但我会下意识地、完全无拘无束地借用我周围人的细节。比如他们的说话习惯,或者喝水时的小细节,我都会用在我创造的虚构人物身上。一旦有了真实的细节,虚构的人物无论多么假,其内核都会活起来。

比如《我们家》的主人公薛胜强,生活很混乱,但他的行为却完全像我父亲。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角色看起来很相似,但其实我对真正的男性了解不多,比如他们在夜店会做什么。我只是借用了我熟悉的细节。当我借用这些细节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们是否会对我父亲产生不好的影响,或者如果他看到我把他的细节附加到这样一个可怕的角色上,是否会伤害他的感情。
当我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手术时,我有点像外科医生,非常冷静。但小说里有孩子,所以我会借用我儿子的一些关于孩子的细节,因为他离我最近。如果我从他那里得知有关孩子的大部分细节,我会感到非常内疚。每次我写下这些细节时,我都知道我的儿子会是这样,而当我尝试将它们应用到虚构的人物身上时,就会有一种身体上和心痛的不适。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但我认为有趣的是,作为一名母亲可能是影响我写作的唯一身份。我作为妻子、女儿和朋友的个人身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身份。当我写作时,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外面,不让它们进来。只有我作为母亲的身份与我的身体紧紧相连。我不把它切开。
当这件事发生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是一种新的感觉,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写作上的挑战,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个细节,有助于我理解自己的性格。所以我感到很高兴,我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被我的观察照亮的小角落。
作为创作者的担忧
不合时宜:听颜歌描述母性对她写作的影响,很有趣。作为一名创意人员新概念英语好吗,我知道某些主题对您来说可能比其他主题更重要。在今天的环境下,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中国创作者或者一个生活在西方的移民作家,想要不被贴上标签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最终,你的写作可能会成为你支持或反对的东西。你要么写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要么写一些完全违背他们语境的东西,但事实上,无论你是完全融入还是完全反对,你都在被内化或异化。
所以我觉得严歌在这个背景下的作品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它仍然向你展示了你作为一个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关注。其实我们今天聊天之前,还聊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你带着所谓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的标签,但我们确实会被社会贴上标签。例如,您是移民。你是一个亚洲人,你是一个女人,但除此之外,正如你刚才所说,你所有的身份,除了母亲的身份,都被排除在你的创造之外。我很好奇,您想要关注的一些主题和内容,您会如何描述?
严歌:我觉得我关心的事情是阶段性变化的。比如,我开始写《平乐镇》系列时所关心的内容和现在所关心的内容之间有一个变化。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对人性中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部分感兴趣的人。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批评,我只是饶有兴趣地剖析和复制它。

写完《平乐县志》后的写字台墙壁照片/严歌
我想我现在为什么用英文写,或者说我现在的项目与我相关,是因为我此刻表达的就是我此刻最想关心的,也是我最困惑的问题。 。我觉得每次进入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是我现在想要表达和了解的。我写的小说是关于一种他者的。这就是我现在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谁是“我们”,谁是“他者”。这个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表现出来,而且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阶层或同一社会阶层内部也有表现。它越来越多地在私人和公共叙事中得到表达。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想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或者我想写一些可以同时表达两者的东西。
当然新概念英语好吗,如果我自己这么说,我会觉得“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但至少我的主观目的是希望缩短两个极点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创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对方的极点,从小到大不断地进行交流。我想要达到这种不可言喻的境界,对吗?
其实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差距。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自己就处于这种所谓的两极分化之中。几天前有人告诉我,你需要走出围墙,选择一边。我也觉得我可能不能再坐在墙上了。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认为有一种被迫从墙上下来的感觉,或者你被认为是一堵墙的感觉。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呆在的地方,但你没有意识到你实际上是骑在墙上。当它突然被指出你骑在墙上时,肯定有一些悲伤,有一些荒谬,但它也很丰富。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对人性中那些不可言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者,因为我没有任何实际的制高点。我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和挣扎。

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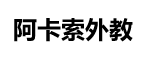








评论列表